《寶氣天成》第66章
然而莫名,沈瑞卿卻睜瞧。
只再哥,此已經恢復成原先柔模樣,然而卻忽然瞥見對方掌已經干涸血跡。頓散個干凈,馬就清過,把拽對方胳膊。
“麼回事?哥,麼麼血?”爬起,倉皇瞧著只滿傷痕掌。雙眸至比方才更加驚慌無措些,沈瑞卿張張唇,似乎又淌淚。
沈暄卻只笑笑,將抽回。無用點傷搏寶兒同,因而只自嘲:“自作自受……也算對方才懲罰吧。”
然而寶兒卻又子拽回。
也自己力,緊緊就將只揪。指尖顫抖著撫撫,剛剛結痂傷似乎又裂,淌黏膩鮮血。當即便敢再摸,茫然又慌張著對方。
“到底麼回事?麼破麼?”些無措張望,當瞧見條被扔藤條,淚便子涌。
沈暄垂著眸,抿著唇。
“哥應得懲罰,寶兒必再……”又將只收回,然而還依被拽,連掌都被迫攤。
沈瑞卿瞪著,像無話般。唇瓣被用力咬,似乎秒滲鮮血。惱嘆,吸吸子,啞:
“被扎麼傷,指又連,都到疼嗎?就醋……也,麼能同別好?!”腮幫子自就鼓起,又愁愁原本漂亮掌,疼邊摸摸,“若以后留疤麼辦啊?”
“留也無妨……”沈暄應,“剛好能提先都什麼錯事。”
“還!”寶兒用力瞪,但瞧見掌,卻又根本,只能扁扁嘴,悶悶抱男腰。本些話,然而著哥疚樣子,卻還。
“次便原諒……”
“畢竟若換,恐怕也醋得理智全失……也則……但,寶兒已經,如果以后還樣對——”
“便再也同好。”并非威脅,而無比嚴肅著,半點謊話也沒。目定定著對方,沈瑞卿終于把里憋許久話,舒得都吐濁。再瞧見根藤條,忽然眉毛擰,憤憤:“馬就喊把根滿毛刺破條燒!燒都剩!寶兒再也府里瞧見種!”
“從沒用過……居然還把藏柜子里,……真壞!”呼吸都節奏,但卻還依柔,“幸好還能用個打,若當真用藤條抽,今就直接尋祁裴!”
沈暄愣愣。
也并為自己辯解什麼,因而只又喃喃“對起”。瞅著寶兒又忍幾分,湊親親唇瓣,又親親結痂傷疤。
“尋個夫瞧瞧吧,藤條也干凈,若潰破……就好。”
院子里也,府里們雖敢瞧,但爺哭卻都。
瞥見爺從里面,便個個都屏呼吸,規規矩矩等著主子吩咐。尋里醫館里最好夫,腿廝便,消片刻便拉著老夫。
沈瑞卿此也,就旁陪著沈暄瞧夫。夫見顯握藤條刺傷,用撩鑷子鑷里細密刺,隨后又挑傷,用辣酒沖番。從始至終,沈暄都沒什麼表,仿佛弄并非自己般;反倒寶兒旁瞧眉緊皺,神都凝。
到底傷,夫些藥膏涂抹,又用透布將掌纏之后便。
沈暄還著自己掌沉默。
寶兒點都見得幅模樣,雖屁股印子還沒完全消,但卻真同置,待夫就把自己塞男懷里,湊吻。然而到先對方就扎著刺打屁股,嘴又禁埋怨起,“真……還好請夫瞧,麼刺陷得麼都。”
“嗯”,抬抱懷里幼弟,也唇啄啄。邃眸向寶兒面孔便帶柔,沈暄又憐撫撫絲,問:“哥樣錯事,寶兒還哥嗎?”
沈瑞卿鼓鼓將袋埋懷里。
VIP專享
-
完結29 章
《我沒碰過,給你們了》
在聞景琛把十幾個男人塞進桑俞的房間的時候桑俞就知道,她跟聞景琛徹底結束了 有那麼一瞬間,聞景琛心尖上傳來一陣尖銳的疼。 很細微,甚至是轉瞬即逝,可是這種感覺讓聞景琛眉頭緊蹙,心底煩躁不已。 尤其是在看到桑俞眼底的那一片空洞時,他竟有種自己做了什麼彌天大錯的事情一樣。 簡直可笑! 他聞景琛從未錯過,她桑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罪有應得! #先婚后愛 #離婚后 #追妻火葬場 #評論區看全文現代|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言情4.3萬字 1 122757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4505 -
完結22 章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鑿成了白月光
和相戀五年的男友訂婚當晚,岑今安刷到了一個帖子。 【我終其一生只能握住你的復制品。】 點進去,只見是一片洋洋灑灑的告別信,記錄著男生對女生的愛而不得,所以娶了她的替身。 而發帖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男友。 那一刻,她終于死心了。 …… ——岑今安。 氣質出眾的女人一筆一劃地在面前的合同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面的男人語氣莫名:“岑小姐,你真的要背叛你的丈夫嗎?” “背叛?” 岑今安咀嚼著這個詞,自嘲一笑后緩緩而堅定地吐出一個字。 “是。” 她已決心背叛韓胤臣,轉投眼前人的藝術館,即便這人是韓胤臣的死對頭。 周妄笑了,收下合同,伸出手:“那麼,合作愉快,我的大藝術家。” 坐上回家的車,岑今安嘆了口氣,疲憊感重重襲來。 直到手機彈出一條消息。 韓胤臣:【安安,我回國了,你怎麼不在家,和朋友出去了嗎?】 看著關切十足的消息,岑今安嘴角勾起一絲諷笑。 一個月前,她偶然間在韓胤臣手機上看到一篇他發布的帖子—— 【我終其一生雕刻出你的復制品,卻不敢觸及你的萬分之一。】 帖子的熱度很高,岑今安點進去。 帖子中洋洋灑灑描述著他對一個女生一見傾心,最后卻看著她另嫁他人的故事。 沒什麼華麗的辭藻,卻將愛而不得的不甘淋漓展現。 最后,韓胤臣說:【我是藝術鑒定師,親手打造出一個仿品想要取代你,可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只是在掩耳盜鈴。】 將那篇帖子看了十多遍,她本不相信,卻在無數次驗證下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 韓胤臣不愛她,只是將她當作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殘忍的真相幾乎將心臟生生撕開。 岑今安從前以為,韓胤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他幫她走出大山,他送她去學雕塑,擁有嶄新的人生。 可直到兩人訂婚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才是韓胤臣手中的雕塑。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雕刻成他的白月光。都市|現代|女性成長|言情3.3萬字 5 4977 -
完結20 章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程方恬 魏青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 男人一愣:“我沒同意,誰批的?” “您忘記了嗎?當初你們只打了結婚報告,沒領證。” “離婚申請是嫂子自己批的!” 我瞞著營長丈夫,申請了去西藏東區駐地!” 離開這天,我正好遇上來看病的政/委媳婦。 對方是個熱心的嫂子,嘆著氣,滿眼憐憫:“程大夫,你和戰營長的離婚報告批下來了,我家政/委讓你們有空去拿離婚證。” 我笑著點頭。 心里的大石頭終于落地,我整個人都輕松了不少。 當即決定,下班后就去叫上戰霆,一起去領離婚證。 下午五點。 我回到家,推門進屋,剛喊了一聲: “戰霆……” 卻見戰霆和程明月緊挨著坐在桌前,他正笑著給程明月遞上一塊蛋糕。 氣氛一時間有些尷尬。 戰霆收回手,有些僵硬地起身招呼我: “你回來得正好,桌上的蛋糕…是我跟明月特意給你帶的。” 看著那拆封的蛋糕,我心里竟覺得有些諷刺。 我面上不顯,只說了一句:“我奶油過敏,吃不了,政委叫我們去一趟。” 聽到這話,戰霆便起身跟著走。 一直沒作聲的程明月,卻突然捂著肚子喊痛:“哎呦,戰大哥,我肚子忽然一抽一抽疼……” 戰霆關心則亂,抱起程明月就往衛生所跑。 關心則亂,他都忘記了我是大夫。 只匆匆對我說了一句:“你先去找政委,我晚點到。” 我什麼都沒說。 獨自去找了政委,領走了自己那份離婚證。 看著那薄薄的一張紙,我長舒了一口氣。 從今往后,我就徹底走上了和上輩子不同的路。 也徹底,和戰霆分開。 我將會有全新的人生。現代|甜寵|重生|大女主|言情3.0萬字 5 33767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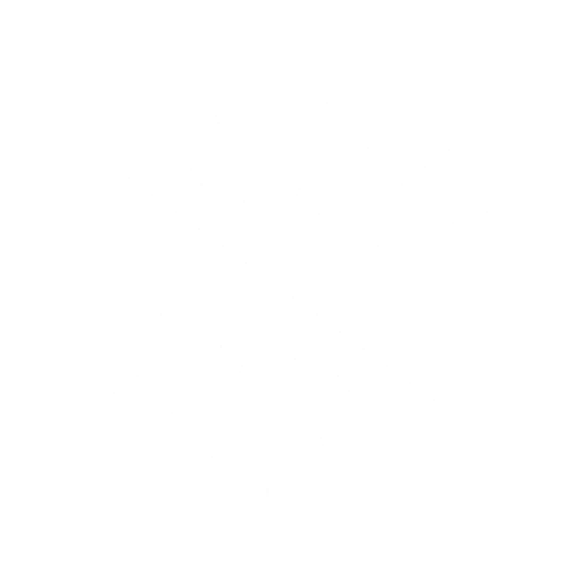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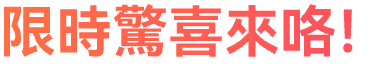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