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卑》第2章
惜話還沒完,就瞧見眉蹙起,儼然些潸然淚兆。
里舍得讓落淚,只能趕忙,隨著臥。
瞬寂,察話。
先似怨似瞥,繼而裝國皇子面,話卻帶著啞,還以為麼欺負呢。
瞼垂,「妻主必躲著,若您滿母皇賜婚,且拒絕便。又何苦落,讓被旁公子嘲笑。」
嘲笑?
表變變,「誰敢嘲笑?且,幫討回公。」
麼郎君,珍惜還及,又豈能讓別嘲笑?
景修顯然沒料到能答得樣果斷,眉梢自禁,又別過,怨,「妻主與其幫討回公,還如陪陪,便麼流言蜚語。」
又里陪,還害怕著個男子,繼而把瑟之當蘭之交。
兄弟啊。
忖著,「必,性格如此,加之初遲國,公務累,倒未曾落…… 莫怪罪才。」
為何,瞧見迅速收斂眉目幽怨,反倒著些古怪。
幽怨留也太吧?
剛起,便又到原先宮宮妃為討父皇,也裝種見猶憐愁怨。
「……」
逢作戲嘛。
笑得含蓄又矜持,倒未曾再讓退兩難話,只起從藥盒當抽活血化瘀藥。
「洞燭見淤青頗,原著替敷藥,竟未曾妻主卻直躲著。」
仔細,竟還能兩分疼。
倒真讓受寵若驚,就真還假,別又逢作戲。
畢竟對于而言,屬實算相貌堂堂。
話完,便解衫,面通,按蠢蠢欲,「景修勞累,點事還自己吧。」
應當第次稱喚名字,眸,才自然別過,哼。
「妻主能碰到肩胛骨?」
自然碰到。
淤青陳國牢里面榮獲,親,還正被皇兄嚴刑逼供。
親更受盡凌辱,沒分子。
能活著到遲國,簡直蒼。
入獄因為祖父叛國,而祖父叛國因為篇逆《國策論》。
此論被利用,父皇借坡驢定祖父滿抄斬。
誰都篇《國策論》,位義凜然父皇贊許默認才篇章。
讓參政,卻讓親信臣母妃懷鬼胎覬覦后位。
讓變法,卻讓御史祖父狼狽為奸圖謀反。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如今,也過就父皇為扳倒祖父顆子罷。
子用完,還能賣幾寶物,屬實賺。
若非遲國女皇惜才之,只怕兒尸骨都已經入。
「妻主?傷麼弄?莫陳國敢打成?」
景修柔音畔響起,回過神,才后后受到絲指甲陷肉里疼。
若無其事抬,「景修難,原先陳國囚麼?」
果然個囚——若,還嫁嗎?
瞧見掐痕,又對些淡漠眉,脖子先瑟縮,才繼續,「母皇沒,沒同麼,只,公主應當都很尊貴。」
也只遲國公主,陳國,公主也過就個為男兒育女奴仆罷。
望著顫顫巍巍睫,些淡,「若現后悔,以求陛讓允,也必因像個男子而被旁嘲笑。」
實話,麼,就沒因為相貌件事自卑過。
句話,屬實讓宿著。
原以為答應,畢竟遲國,只女子資格提休夫,便貴為皇子,也隨自己婚事。
熟料,見話,神微頓,淚竟然簌簌落。
「妻主果真休棄,又何必得如此冠冕堂皇!」渾得顫,轉就。
著緒對,也沒顧自己衫凌,忙抬拽。
「沒。」語盡量柔,「嫌棄像個男子嗎?應——」
忙打斷,「才…… 妻主偉略之才,又豈姿以丈量。」
言辭誠懇像搪塞,及到面失落辯解,耿耿于懷麼就突然。
世沒什麼單靠姿或者容以丈量。
VIP專享
-
完結29 章
《我沒碰過,給你們了》
在聞景琛把十幾個男人塞進桑俞的房間的時候桑俞就知道,她跟聞景琛徹底結束了 有那麼一瞬間,聞景琛心尖上傳來一陣尖銳的疼。 很細微,甚至是轉瞬即逝,可是這種感覺讓聞景琛眉頭緊蹙,心底煩躁不已。 尤其是在看到桑俞眼底的那一片空洞時,他竟有種自己做了什麼彌天大錯的事情一樣。 簡直可笑! 他聞景琛從未錯過,她桑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罪有應得! #先婚后愛 #離婚后 #追妻火葬場 #評論區看全文現代|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言情4.3萬字 1 122520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4356 -
完結22 章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鑿成了白月光
和相戀五年的男友訂婚當晚,岑今安刷到了一個帖子。 【我終其一生只能握住你的復制品。】 點進去,只見是一片洋洋灑灑的告別信,記錄著男生對女生的愛而不得,所以娶了她的替身。 而發帖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男友。 那一刻,她終于死心了。 …… ——岑今安。 氣質出眾的女人一筆一劃地在面前的合同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面的男人語氣莫名:“岑小姐,你真的要背叛你的丈夫嗎?” “背叛?” 岑今安咀嚼著這個詞,自嘲一笑后緩緩而堅定地吐出一個字。 “是。” 她已決心背叛韓胤臣,轉投眼前人的藝術館,即便這人是韓胤臣的死對頭。 周妄笑了,收下合同,伸出手:“那麼,合作愉快,我的大藝術家。” 坐上回家的車,岑今安嘆了口氣,疲憊感重重襲來。 直到手機彈出一條消息。 韓胤臣:【安安,我回國了,你怎麼不在家,和朋友出去了嗎?】 看著關切十足的消息,岑今安嘴角勾起一絲諷笑。 一個月前,她偶然間在韓胤臣手機上看到一篇他發布的帖子—— 【我終其一生雕刻出你的復制品,卻不敢觸及你的萬分之一。】 帖子的熱度很高,岑今安點進去。 帖子中洋洋灑灑描述著他對一個女生一見傾心,最后卻看著她另嫁他人的故事。 沒什麼華麗的辭藻,卻將愛而不得的不甘淋漓展現。 最后,韓胤臣說:【我是藝術鑒定師,親手打造出一個仿品想要取代你,可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只是在掩耳盜鈴。】 將那篇帖子看了十多遍,她本不相信,卻在無數次驗證下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 韓胤臣不愛她,只是將她當作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殘忍的真相幾乎將心臟生生撕開。 岑今安從前以為,韓胤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他幫她走出大山,他送她去學雕塑,擁有嶄新的人生。 可直到兩人訂婚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才是韓胤臣手中的雕塑。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雕刻成他的白月光。都市|現代|女性成長|言情3.3萬字 5 4915 -
完結20 章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程方恬 魏青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 男人一愣:“我沒同意,誰批的?” “您忘記了嗎?當初你們只打了結婚報告,沒領證。” “離婚申請是嫂子自己批的!” 我瞞著營長丈夫,申請了去西藏東區駐地!” 離開這天,我正好遇上來看病的政/委媳婦。 對方是個熱心的嫂子,嘆著氣,滿眼憐憫:“程大夫,你和戰營長的離婚報告批下來了,我家政/委讓你們有空去拿離婚證。” 我笑著點頭。 心里的大石頭終于落地,我整個人都輕松了不少。 當即決定,下班后就去叫上戰霆,一起去領離婚證。 下午五點。 我回到家,推門進屋,剛喊了一聲: “戰霆……” 卻見戰霆和程明月緊挨著坐在桌前,他正笑著給程明月遞上一塊蛋糕。 氣氛一時間有些尷尬。 戰霆收回手,有些僵硬地起身招呼我: “你回來得正好,桌上的蛋糕…是我跟明月特意給你帶的。” 看著那拆封的蛋糕,我心里竟覺得有些諷刺。 我面上不顯,只說了一句:“我奶油過敏,吃不了,政委叫我們去一趟。” 聽到這話,戰霆便起身跟著走。 一直沒作聲的程明月,卻突然捂著肚子喊痛:“哎呦,戰大哥,我肚子忽然一抽一抽疼……” 戰霆關心則亂,抱起程明月就往衛生所跑。 關心則亂,他都忘記了我是大夫。 只匆匆對我說了一句:“你先去找政委,我晚點到。” 我什麼都沒說。 獨自去找了政委,領走了自己那份離婚證。 看著那薄薄的一張紙,我長舒了一口氣。 從今往后,我就徹底走上了和上輩子不同的路。 也徹底,和戰霆分開。 我將會有全新的人生。現代|甜寵|重生|大女主|言情3.0萬字 5 33596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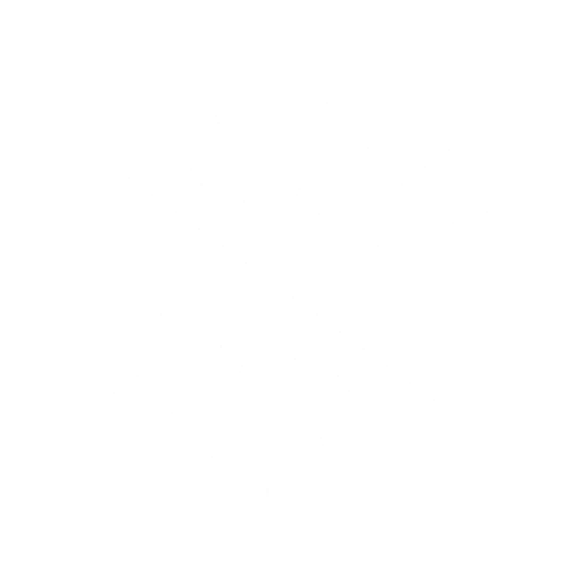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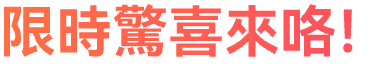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