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氏雜記》第34章
抓起散物,搭腿。雖然驚恐至極,但事倒仍未失條理。
“為什麼?”用按胸,踞跪,赤著端正挺。
“嗎……”艱難問。
“,麼呢。”沈晏周略施功,雙落。隨即屏青袍旋,披而起。
“畢竟弟,麼。只過該已經完,沒再陪演,”沈晏周穿好物,后用繩豎起,如當倦刀主初入打扮,透著股凜冽颯爽,“咳疾愈,沒精力治理業,坡,連薛豎子都敢言挑釁。虧弟回夜操勞,把商鋪打理得妥妥帖帖。”
“只福祿王爺捐未免點,作為沈主,為兄得些肉痛,”沈晏周抱臂站傅清寒面,打量著,“對放權麼久,也候收回。兩個煩跟班終于,現正適嗎?”
“……利用,用完再腳踢?”傅清寒額浮起汗,用兩個膝蓋后退,盡量男,“肯主位子,也為今兔狗烹?”
沈晏周似笑非笑往踱步,傅清寒只顧膝后退。
“信……”傅清寒退無退,把按皙冰涼赤裸腳背,眶通語,“因為,定為報復!”
“哥,傷,以報復,”傅清寒微垂著,“以,也以把起……些都……都沒系。
”
沈晏周失笑,勾起傅清寒巴,挑起眉梢,“清寒,弟弟,為什麼?真話,能點討厭。”
“爹娶娘親,娘因此郁郁寡。娘親病逝過,爹就酗酒墜而。平個弟弟,毫無血緣系,卻分沈產,”沈晏周聳聳肩,“清寒,討厭嗎?”
“為什麼對好……”傅清寒盯著睛。
沈晏周笑,“因為無依無靠啊,稍微對好點,就像只狗樣貼過沖搖尾巴,真很趣。”
“只過被自己養狗咬,讓點。就試試,如果再讓,然后把腳踢,什麼表呢?”沈晏周捂嘴笑起,只撫撫傅清寒頰,“表錯哦,弟。”
“,個字也信。”傅清寒渾寒戰,突然俯嘔吐起。
吐得狼狽堪,穢物濺沈晏周腳。沈晏周厭惡皺皺眉,抬起腳擦拭。
臟已經疼痛到麻,連淚都流。傅清寒撐著抬起,抱沈晏周腳貼自己,“哥哥……好難過…………”
“……以,以很嗎……”傅清寒把額靠沈晏周膝蓋,只握,瘋狂摩擦。
象征毫無反應,如同受驚物般萎靡振。作過于急躁粗暴,表面很變,隱隱滲血絲。
沈晏周垂眸瞥著,目逐漸凌厲起。
猛然抬腳將傅清寒踢。
傅清寒從里摔落到院,幾朵梅絹被震落,飄到。
“真夠副丑態,弟,點吧。”沈晏周也院子,面已耐。
“……讓?”傅清寒怔怔。
“個姓沈,姓傅。”沈晏周無奈過,脫青袍,披肩膀。端詳著傅清寒片,貼著朵笑:“……除非再被鎖起玩弄,就自己打根鏈子,也以勉為其難再陪玩玩。”
傅清寒瞳孔驀縮,劇烈震,嘔鮮血。
“,把傅清寒扔。從今以后,沈就沒個。”沈晏周隨拍拍,兩個丁從何處,后抬起傅清寒肢。里丁兩仿佛對傅清寒惟命從,卻種候絲毫敢違背沈晏周,即使如此荒唐命令。
傅清寒被兩抬,目卻固執肯移。沈晏周注到盯,忽然抬,掌打梅干。
“喀嚓”巨響,株院梅從主干折斷,轟然倒。絹散落,如鮮血涌。
沈晏周妄真,似乎受到反噬,子由自主搖晃。轉過向傅清寒。
傅清寒收回目,絕望閉睛,淚終于滾滾而落。
著被丟院子,何從墻。福穿過梅,到沈晏周旁,“爺,就麼把趕,怕福祿王?”
“福祿王收留,因為們交易。
”沈晏周淡淡。
福突然敢再問什麼。
“把滿杈收拾。
VIP專享
-
完結29 章
《我沒碰過,給你們了》
在聞景琛把十幾個男人塞進桑俞的房間的時候桑俞就知道,她跟聞景琛徹底結束了 有那麼一瞬間,聞景琛心尖上傳來一陣尖銳的疼。 很細微,甚至是轉瞬即逝,可是這種感覺讓聞景琛眉頭緊蹙,心底煩躁不已。 尤其是在看到桑俞眼底的那一片空洞時,他竟有種自己做了什麼彌天大錯的事情一樣。 簡直可笑! 他聞景琛從未錯過,她桑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罪有應得! #先婚后愛 #離婚后 #追妻火葬場 #評論區看全文現代|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言情4.3萬字 1 122449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4317 -
完結22 章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鑿成了白月光
和相戀五年的男友訂婚當晚,岑今安刷到了一個帖子。 【我終其一生只能握住你的復制品。】 點進去,只見是一片洋洋灑灑的告別信,記錄著男生對女生的愛而不得,所以娶了她的替身。 而發帖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男友。 那一刻,她終于死心了。 …… ——岑今安。 氣質出眾的女人一筆一劃地在面前的合同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面的男人語氣莫名:“岑小姐,你真的要背叛你的丈夫嗎?” “背叛?” 岑今安咀嚼著這個詞,自嘲一笑后緩緩而堅定地吐出一個字。 “是。” 她已決心背叛韓胤臣,轉投眼前人的藝術館,即便這人是韓胤臣的死對頭。 周妄笑了,收下合同,伸出手:“那麼,合作愉快,我的大藝術家。” 坐上回家的車,岑今安嘆了口氣,疲憊感重重襲來。 直到手機彈出一條消息。 韓胤臣:【安安,我回國了,你怎麼不在家,和朋友出去了嗎?】 看著關切十足的消息,岑今安嘴角勾起一絲諷笑。 一個月前,她偶然間在韓胤臣手機上看到一篇他發布的帖子—— 【我終其一生雕刻出你的復制品,卻不敢觸及你的萬分之一。】 帖子的熱度很高,岑今安點進去。 帖子中洋洋灑灑描述著他對一個女生一見傾心,最后卻看著她另嫁他人的故事。 沒什麼華麗的辭藻,卻將愛而不得的不甘淋漓展現。 最后,韓胤臣說:【我是藝術鑒定師,親手打造出一個仿品想要取代你,可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只是在掩耳盜鈴。】 將那篇帖子看了十多遍,她本不相信,卻在無數次驗證下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 韓胤臣不愛她,只是將她當作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殘忍的真相幾乎將心臟生生撕開。 岑今安從前以為,韓胤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他幫她走出大山,他送她去學雕塑,擁有嶄新的人生。 可直到兩人訂婚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才是韓胤臣手中的雕塑。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雕刻成他的白月光。都市|現代|女性成長|言情3.3萬字 5 4894 -
完結20 章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程方恬 魏青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 男人一愣:“我沒同意,誰批的?” “您忘記了嗎?當初你們只打了結婚報告,沒領證。” “離婚申請是嫂子自己批的!” 我瞞著營長丈夫,申請了去西藏東區駐地!” 離開這天,我正好遇上來看病的政/委媳婦。 對方是個熱心的嫂子,嘆著氣,滿眼憐憫:“程大夫,你和戰營長的離婚報告批下來了,我家政/委讓你們有空去拿離婚證。” 我笑著點頭。 心里的大石頭終于落地,我整個人都輕松了不少。 當即決定,下班后就去叫上戰霆,一起去領離婚證。 下午五點。 我回到家,推門進屋,剛喊了一聲: “戰霆……” 卻見戰霆和程明月緊挨著坐在桌前,他正笑著給程明月遞上一塊蛋糕。 氣氛一時間有些尷尬。 戰霆收回手,有些僵硬地起身招呼我: “你回來得正好,桌上的蛋糕…是我跟明月特意給你帶的。” 看著那拆封的蛋糕,我心里竟覺得有些諷刺。 我面上不顯,只說了一句:“我奶油過敏,吃不了,政委叫我們去一趟。” 聽到這話,戰霆便起身跟著走。 一直沒作聲的程明月,卻突然捂著肚子喊痛:“哎呦,戰大哥,我肚子忽然一抽一抽疼……” 戰霆關心則亂,抱起程明月就往衛生所跑。 關心則亂,他都忘記了我是大夫。 只匆匆對我說了一句:“你先去找政委,我晚點到。” 我什麼都沒說。 獨自去找了政委,領走了自己那份離婚證。 看著那薄薄的一張紙,我長舒了一口氣。 從今往后,我就徹底走上了和上輩子不同的路。 也徹底,和戰霆分開。 我將會有全新的人生。現代|甜寵|重生|大女主|言情3.0萬字 5 33528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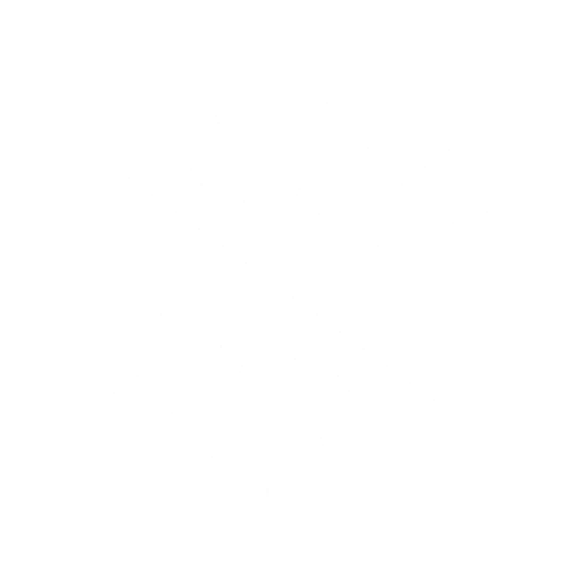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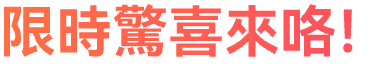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