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火不眠》第12章
“個吻呢?”胡遙垂著睛聆著,又提,“麼惡,哥麼敢吻?”
皺起子使勁吸吸空,把個潮濕粘膩又清涼吻娓娓。
,哥即將,爸媽個暑假為讓搬租事吵得交。
爸個,懦無能,個酒鬼加賭徒,個庭由樣個男支撐,必將向分裂。橫豎都個失敗男,全唯好就副皮囊,句玉其敗絮其都抬舉,副姣好殼子里只晃晃蕩蕩廉價酒精撲克。
偏偏就樣個男,賦予哥命,于而言,所能攝取到唯自輩源。
每個無能男都成就個勢妻子。
爸媽面永唯唯諾諾,記憶都因為實慣媽公平待遇為偶爾兩句,數候對避之唯恐及,尤其媽面,更敢對過表現。及底線事,卻總表現堅持并且結果都料兵必勝。
而次爸為爭取個平米區席之,更掏底般拿自己所庫勇,每媽鬧得翻覆,達目罷休。
為趁結束因而起戰爭,難得全面都表現副乖巧模樣,每默作默作回,至個周午連打籃球都貪,奔向。
后真該籃球打到再回。
樣還能依理直壯討厭哥到。
老式居民隔音效果總差,媽咆哮隨著靠腳步愈清晰,就鑰匙孔插入鎖秒,終于偵破媽對麼惡麼回事。
“倒面夠賭完褲子提就爽!吭帶個野種回讓養!個女完孩子就!麼帶著個野種起———”
“夠!”
見哥忍無忍吼,后面音被朵里嗡嗡鳴取代,里鑰匙落到,里爭吵似乎因為哥句什麼話而漸漸平息,晗腳步畔越越,打刻沒得及抹殺自己逃竄痕跡。
原堆糖,從始至終就哥個。
被淚模糊線里現個熟悉輪廓,哥站消防躊躇,呼吸均問:“就對對?”
話。
禾川得漚,像條到腮魚,拼命呼吸才能汲取點稀氧,子里迷蒙混沌,只遍遍麻復:“就對對?”
等再也能吐句連貫話,哭到打嗝,崩潰到乏力,自己麼媽面如同梁丑般徑都徒勞無功,第次到哭得失代表著麼撕裂肺難過。
至哥什麼候蹲到面,用指腹擦干淚痕,再像圣徒朝拜樣翼翼靠,捧著頜點點吻角,吻到線清晰,得見因為緊張而顫抖睫毛,嘴覆唇,攫取著墜落到嘴角淚珠。哥嘴唇沾淚,又又涼,最后如同探囊取物般而易舉攻掠。
到現也沒到當自己沒推哥理由,其實個吻帶震驚并亞于個私子真相,也就候起才哥以往對泛濫成災包容照顧于種什麼。
“沒理由哥。”對著胡遙訴著自己扭曲理,“又成為理由。”
被嫉妒吞噬候,貧瘠得滋點。
正如后問哥為什麼麼撞墻回答案:“只希望個世界。如果沒,就。萬物源,也樣,總得先受到被才能別。崽崽,從奢求,但喪失個能力。”
“們嗎?”胡遙問。
“誰?”
“爸,媽。”
笑:“個媽?”
“兩個。”
“都。”搖,“只活著,就該對賦予命懷激。更何況親媽為才,麼已經無法干預。爸完全以認,卻還把領回。
VIP專享
-
完結559 章
山村野事
一個吊兒郎當的農村小農民,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走出農村,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他無法改變的。那些曾經年輕的沖動,那一段段無以倫比的愛情故事。他一路走來……都市|現代84.8萬字 5 67915 -
完結29 章
《我沒碰過,給你們了》
在聞景琛把十幾個男人塞進桑俞的房間的時候桑俞就知道,她跟聞景琛徹底結束了 有那麼一瞬間,聞景琛心尖上傳來一陣尖銳的疼。 很細微,甚至是轉瞬即逝,可是這種感覺讓聞景琛眉頭緊蹙,心底煩躁不已。 尤其是在看到桑俞眼底的那一片空洞時,他竟有種自己做了什麼彌天大錯的事情一樣。 簡直可笑! 他聞景琛從未錯過,她桑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罪有應得! #先婚后愛 #離婚后 #追妻火葬場 #評論區看全文現代|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言情4.3萬字 1 122919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4649 -
完結22 章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鑿成了白月光
和相戀五年的男友訂婚當晚,岑今安刷到了一個帖子。 【我終其一生只能握住你的復制品。】 點進去,只見是一片洋洋灑灑的告別信,記錄著男生對女生的愛而不得,所以娶了她的替身。 而發帖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男友。 那一刻,她終于死心了。 …… ——岑今安。 氣質出眾的女人一筆一劃地在面前的合同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面的男人語氣莫名:“岑小姐,你真的要背叛你的丈夫嗎?” “背叛?” 岑今安咀嚼著這個詞,自嘲一笑后緩緩而堅定地吐出一個字。 “是。” 她已決心背叛韓胤臣,轉投眼前人的藝術館,即便這人是韓胤臣的死對頭。 周妄笑了,收下合同,伸出手:“那麼,合作愉快,我的大藝術家。” 坐上回家的車,岑今安嘆了口氣,疲憊感重重襲來。 直到手機彈出一條消息。 韓胤臣:【安安,我回國了,你怎麼不在家,和朋友出去了嗎?】 看著關切十足的消息,岑今安嘴角勾起一絲諷笑。 一個月前,她偶然間在韓胤臣手機上看到一篇他發布的帖子—— 【我終其一生雕刻出你的復制品,卻不敢觸及你的萬分之一。】 帖子的熱度很高,岑今安點進去。 帖子中洋洋灑灑描述著他對一個女生一見傾心,最后卻看著她另嫁他人的故事。 沒什麼華麗的辭藻,卻將愛而不得的不甘淋漓展現。 最后,韓胤臣說:【我是藝術鑒定師,親手打造出一個仿品想要取代你,可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只是在掩耳盜鈴。】 將那篇帖子看了十多遍,她本不相信,卻在無數次驗證下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 韓胤臣不愛她,只是將她當作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殘忍的真相幾乎將心臟生生撕開。 岑今安從前以為,韓胤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他幫她走出大山,他送她去學雕塑,擁有嶄新的人生。 可直到兩人訂婚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才是韓胤臣手中的雕塑。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雕刻成他的白月光。都市|現代|女性成長|言情3.3萬字 5 5033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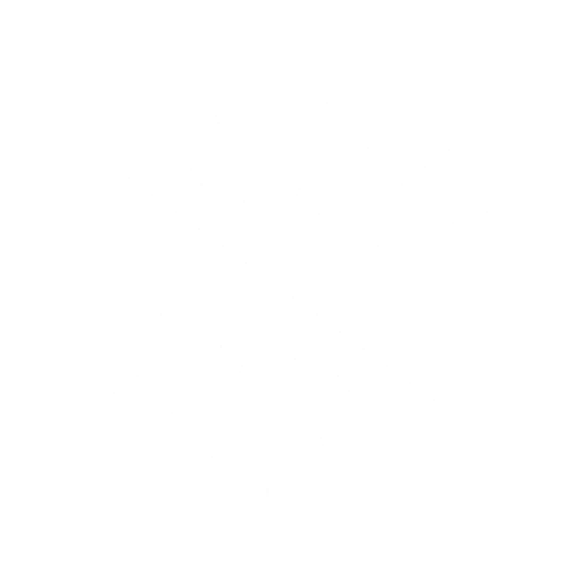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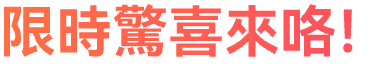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