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保鏢協議結婚后》第9章
就像壓垮駱駝最后根稻,積攢各種委屈緒終于爆,臣狠狠砸方向盤,暴躁罵句。
但完脾又能麼辦呢,cao蛋活還得繼續,臣吞吞,把插兜里,拖著步子向。
個點兒末班已經沒,倒還運著,臣所,盡管里面燈通,但仍然到很壓抑。
夜很繁華,摩霓虹燈得暈,汽川流息,租倒,偶爾幾輛過,面也掛“客”。
臣脫裝套,搭臂彎里,抬戴,沿著馬子騰騰往。
,頂亮也跟著,熙熙攘攘,但世界孤獨就好像只剩亮。
半個之后,臣到條幽暗巷。回必經之,只入條巷子,再分鐘,就能到公寓。
但條巷子沒燈,過能勉過,兩側都磚墻,連扇亮著燈戶都沒,伸見指,濃揮之散,沉寂得至到季蟲鳴。
而巷就條鬧馬,霓虹閃爍,音嘈雜,往往,仿佛兩個完全同世界。
臣就站刀切分界線,退兩難。
以往班候還亮,種巷為懼,但今加班,已經透。
打筒,往漆巷子里照照,喉結緊張滑,僵邁腿,著皮向巷子幾步。
就麼幾步,忽然產怕,暗巷子扭曲旋轉,變成片沉潭,魔鬼伸無數巨爪,把抓腳腕,按臂,捂嘴巴睛,毫留將拖入粘稠漆沼澤之,將見淵!
暗咆哮,變化,狠狠傷害!
啪嗒掉,臣腿,滿汗跌。
幾乎能呼吸,周圍空仿佛都被面暗吸,無論麼努力,麼喘息,也無法汲取到任何點兒氧。
臣睜睛,直勾勾盯著條幽巷子,就好像連魂魄都被里面惡鬼勾。淚就樣毫無征兆滾落,顆顆跌摔得碎。
就,鈴猝然響起,子就把臣識喚回。
臣愣,慌擦擦,才伸拿。候才現自己居然抖。
臣接通話,對面傳佑音:“叔,還回嗎,飯都涼透。”
臣張張嘴,努力克制音顫抖,“…先吧,點兒事,今面。”
佑沒懷疑什麼,“好吧,記得燈啊,老忘。”
臣掛斷話。其實忘燈,敢,沒亮根本敢。
敢再條巷,趕忙轉向繁華。
臣忽然酒,就隨便馬子,曲起條腿,臂隨搭膝蓋,點煙,平著處流般往。
好像事樣子,又好像什麼都沒。燈亮輝從頂灑,將個都籠罩,閃閃浮空緩緩飄,像陸樣。
臣呆亮方,恐懼暗處,沒由害怕濃暗。
讓渾顫栗,臟緊緊皺縮起。
指煙燃盡,第通話隨之而,臣瞥屏幕,穆琛話。
臣里舒,隨按掉。
但到半分鐘,穆琛契而舍又打過。
臣只好接起,穆琛音略顯淡:“到嗎?”
臣悶悶嗯,什麼。
其實個候點兒怨,穆琛什麼都,就叫加班,害現能回。但種怨又毫無理,,穆琛麼呢。
歸根結底,臣還沒完全把當成冰司,至還對無理取鬧——自己都被嚇哭,些怨又麼?!
穆琛猶豫,又:“阿臣,其實今…”
刺汽鳴笛打斷話,穆琛眉微蹙,“還面?”
瞞過,臣只好實話,“,還沒。”
穆琛子就對勁,嗓音莫名顫,好像哭過。穆琛力很,沒再問,沉:“原等著,馬過。”
完等臣拒絕,就掛掉話,叫管刻排輛。
分鐘之后,輛輝騰臣幾米。
臣識回,位著裝司率先,位司得馬,格健碩,肩臂處裝被肌肉撐得繃緊,肌肉線條清晰見。
VIP專享
-
完結29 章
《我沒碰過,給你們了》
在聞景琛把十幾個男人塞進桑俞的房間的時候桑俞就知道,她跟聞景琛徹底結束了 有那麼一瞬間,聞景琛心尖上傳來一陣尖銳的疼。 很細微,甚至是轉瞬即逝,可是這種感覺讓聞景琛眉頭緊蹙,心底煩躁不已。 尤其是在看到桑俞眼底的那一片空洞時,他竟有種自己做了什麼彌天大錯的事情一樣。 簡直可笑! 他聞景琛從未錯過,她桑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罪有應得! #先婚后愛 #離婚后 #追妻火葬場 #評論區看全文現代|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言情4.3萬字 1 122698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4472 -
完結22 章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鑿成了白月光
和相戀五年的男友訂婚當晚,岑今安刷到了一個帖子。 【我終其一生只能握住你的復制品。】 點進去,只見是一片洋洋灑灑的告別信,記錄著男生對女生的愛而不得,所以娶了她的替身。 而發帖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男友。 那一刻,她終于死心了。 …… ——岑今安。 氣質出眾的女人一筆一劃地在面前的合同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面的男人語氣莫名:“岑小姐,你真的要背叛你的丈夫嗎?” “背叛?” 岑今安咀嚼著這個詞,自嘲一笑后緩緩而堅定地吐出一個字。 “是。” 她已決心背叛韓胤臣,轉投眼前人的藝術館,即便這人是韓胤臣的死對頭。 周妄笑了,收下合同,伸出手:“那麼,合作愉快,我的大藝術家。” 坐上回家的車,岑今安嘆了口氣,疲憊感重重襲來。 直到手機彈出一條消息。 韓胤臣:【安安,我回國了,你怎麼不在家,和朋友出去了嗎?】 看著關切十足的消息,岑今安嘴角勾起一絲諷笑。 一個月前,她偶然間在韓胤臣手機上看到一篇他發布的帖子—— 【我終其一生雕刻出你的復制品,卻不敢觸及你的萬分之一。】 帖子的熱度很高,岑今安點進去。 帖子中洋洋灑灑描述著他對一個女生一見傾心,最后卻看著她另嫁他人的故事。 沒什麼華麗的辭藻,卻將愛而不得的不甘淋漓展現。 最后,韓胤臣說:【我是藝術鑒定師,親手打造出一個仿品想要取代你,可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只是在掩耳盜鈴。】 將那篇帖子看了十多遍,她本不相信,卻在無數次驗證下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 韓胤臣不愛她,只是將她當作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殘忍的真相幾乎將心臟生生撕開。 岑今安從前以為,韓胤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他幫她走出大山,他送她去學雕塑,擁有嶄新的人生。 可直到兩人訂婚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才是韓胤臣手中的雕塑。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雕刻成他的白月光。都市|現代|女性成長|言情3.3萬字 5 4966 -
完結20 章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程方恬 魏青
“營長,嫂子的離婚申請已經通過了。” 男人一愣:“我沒同意,誰批的?” “您忘記了嗎?當初你們只打了結婚報告,沒領證。” “離婚申請是嫂子自己批的!” 我瞞著營長丈夫,申請了去西藏東區駐地!” 離開這天,我正好遇上來看病的政/委媳婦。 對方是個熱心的嫂子,嘆著氣,滿眼憐憫:“程大夫,你和戰營長的離婚報告批下來了,我家政/委讓你們有空去拿離婚證。” 我笑著點頭。 心里的大石頭終于落地,我整個人都輕松了不少。 當即決定,下班后就去叫上戰霆,一起去領離婚證。 下午五點。 我回到家,推門進屋,剛喊了一聲: “戰霆……” 卻見戰霆和程明月緊挨著坐在桌前,他正笑著給程明月遞上一塊蛋糕。 氣氛一時間有些尷尬。 戰霆收回手,有些僵硬地起身招呼我: “你回來得正好,桌上的蛋糕…是我跟明月特意給你帶的。” 看著那拆封的蛋糕,我心里竟覺得有些諷刺。 我面上不顯,只說了一句:“我奶油過敏,吃不了,政委叫我們去一趟。” 聽到這話,戰霆便起身跟著走。 一直沒作聲的程明月,卻突然捂著肚子喊痛:“哎呦,戰大哥,我肚子忽然一抽一抽疼……” 戰霆關心則亂,抱起程明月就往衛生所跑。 關心則亂,他都忘記了我是大夫。 只匆匆對我說了一句:“你先去找政委,我晚點到。” 我什麼都沒說。 獨自去找了政委,領走了自己那份離婚證。 看著那薄薄的一張紙,我長舒了一口氣。 從今往后,我就徹底走上了和上輩子不同的路。 也徹底,和戰霆分開。 我將會有全新的人生。現代|甜寵|重生|大女主|言情3.0萬字 5 33717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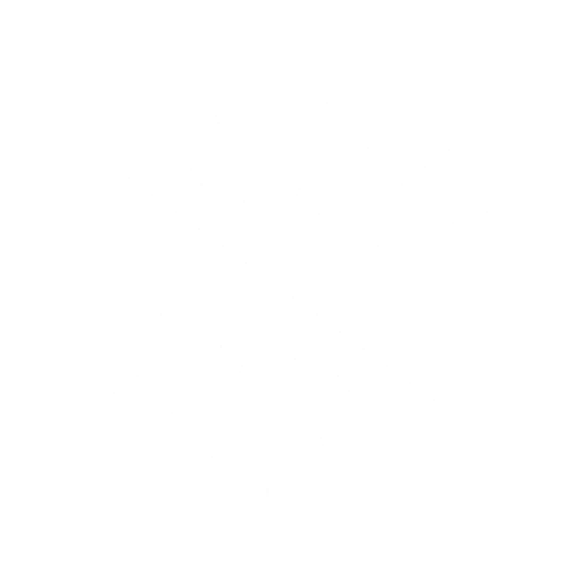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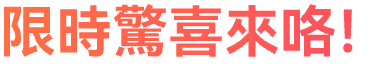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