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身受和白月光he》第129章
“督主,奴才自己便。”蘭澤識往后縮,腳被抓,也躲到里。
謝景庭淡然:“若交蘭澤,興許蘭澤好,耽誤程。”
便變著法笨笨腳,蘭澤聞言起,些,于再。
蘭澤皮膚如皓,骨相好,雙腳比尋常男子些,被握只得弓微繃,顯清瘦線條,腳趾若羊脂骨瓷。
被捏著腳,奇怪順著傳過,讓分清因為還因為別,謝景庭線落面,腳趾自禁略微蜷縮起。
蘭澤對謝景庭面容,謝景庭拿針挑泡,方皮膚,疼痛傳,又疼又癢,蘭澤些難受,識便躲,叫喚。
音又又,還以為貓叫,帶著幾分音,羽毛般撓。
“督主,些疼。”蘭澤些羞恥,自禁起,被抓著腳些所措,識扯謝景庭袖袍。
謝景庭掃,目面頰處略微頓,接作便些,泡點點挑破,蘭澤怕疼,捏著謝景庭袖子躲謝景庭懷里。
等謝景庭為換好棉襪,對:“蘭澤,好。”
蘭澤對尖跟著,些像話,腳趾還蜷著,埋謝景庭懷里略微抬起,雙盈盈濕潤眸,細指尖抓著謝景庭角。
見般,謝景庭用捂睛,對:“如今面,使性子。
”
蘭澤確實撒嬌耍賴犯懶,,就般賴謝景庭懷里。
如今到謝景庭平話音,蘭澤于起,自己理番衫,面常卿已經敲。
蘭澤被吹便清些許,方才興許謝景庭得麻煩,般姿態,蘭澤胡,隨著很到方。
野空曠起,里座祭臺,面圍繞著壁,壁先雕刻瘟神神君與疫災諸鬼。
所謂祭祀儀式,需李謝景庭,鼓鳴鼓,點燃瘟元制成線,把瘟神神君神印熏才算祭祀完成。
瘟神神君像巨壯觀,神君著眉柔慈目,面隱隱青苔與留痕跡,漫歲里痕跡逐漸變得刻。
祭祀儀式只李謝景庭參與,謝景庭驚鴻之貌,持線與臺之,神君與之相比稍顯遜分。
雙平淡無波,仿佛于之,只掃過群某之后,緒便性。
按照原先規矩,個燃完之后另個才。
謝景庭接過線之后并未,而先李。
兩縷線纏繞起,蘭澤站群之,臺兩形顯而清晰,當座現候,蘭澤沒能反應過。
未曾久待,滾落,只邊傳巨嗡鳴,隨著巨滾落,周圍侍紛紛刀劍鞘,臺瘟神神君分裂。
“砰”,隨著巨垂直落,蘭澤見什麼被壓碎壓成音。
宋到邊,蘭澤順著臺,周圍寂片,神君神像,巨攤血跡,還只被砸斷。
蘭澤刻提起,臟略微緊,待清只屬于謝景庭之后,才略微放。
碎塊落,謝景庭臺自然未能幸免,就站李旁,頰被塊劃破,血跡自額往滴落。
隔著騷鬧群與祭臺,臺謝景庭與臺賀玉玄對線。
謝景庭線扔,放腰劍柄,眸像瀾見底淵底。
血跡為張添抹殊艷,驚鴻至極面容,宛如獄邊殘,吞欲,便被表象迷惑,因此陷入萬劫復之境。
“李……李,吶!!”
隨著隨從呼,祭臺巨被力搬,展李被壓變形尸,血跡滲透座祭臺,片。
底起,侍刻將此處守,蘭澤到謝景庭沒事之后略微放,掃李尸,被血腥熏些吐。
孟清凝何到蘭澤邊,著臺尸略些惜,對蘭澤:“蘭澤,聞過活祭?”
蘭澤聞言搖搖,方才嚇得魂都沒,再孟清凝如此淡定,忍問:“什麼?”
“傳聞以往戰代,些神像并作,需祭祀才能護方太平。
而候……通通祭祀都極奸極惡之徒。
VIP專享
-
完結559 章
山村野事
一個吊兒郎當的農村小農民,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走出農村,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他無法改變的。那些曾經年輕的沖動,那一段段無以倫比的愛情故事。他一路走來……都市|現代84.8萬字 5 68030 -
完結29 章
《我沒碰過,給你們了》
在聞景琛把十幾個男人塞進桑俞的房間的時候桑俞就知道,她跟聞景琛徹底結束了 有那麼一瞬間,聞景琛心尖上傳來一陣尖銳的疼。 很細微,甚至是轉瞬即逝,可是這種感覺讓聞景琛眉頭緊蹙,心底煩躁不已。 尤其是在看到桑俞眼底的那一片空洞時,他竟有種自己做了什麼彌天大錯的事情一樣。 簡直可笑! 他聞景琛從未錯過,她桑俞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罪有應得! #先婚后愛 #離婚后 #追妻火葬場 #評論區看全文現代|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言情4.3萬字 1 122926 -
完結20 章
任務歸來,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營長執行任務歸來,發現他那惹人嫌的媳婦變了。 她不再因為男人照顧隔壁的姐姐吃醋, 也不再偷偷摸摸跟蹤男人的行蹤。 她吃好睡好,不哭不鬧。 哪怕男人在隔壁的屋子里徹夜不歸, 她也不鬧脾氣,而是表示理解。 男人以為,自己這半年的冷落,終于換來了她的懂事。 直到那天,他看見了她買的火車票。 “你去首都干什麼?” 她垂在身側的手不自覺收緊。 男人質問她,是在擔心什麼? 是怕她去首都鬧,對江明月不利嗎? 但她還是咽下了到了口中這些話,因為問到答應也沒有意義。 她放下早餐,若無其事上前收起票:“沒什麼,衛生所外派我去學習,我提前準備了車票。” “先吃飯吧。” 她遞上筷子,她的神態太過自然,男人便沒再深究。 隨后又是小半月過去,離開的日子越來越近。現代|女性成長|先婚後愛|追妻火葬場|爽文2.9萬字 5 4654 -
完結22 章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鑿成了白月光
和相戀五年的男友訂婚當晚,岑今安刷到了一個帖子。 【我終其一生只能握住你的復制品。】 點進去,只見是一片洋洋灑灑的告別信,記錄著男生對女生的愛而不得,所以娶了她的替身。 而發帖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男友。 那一刻,她終于死心了。 …… ——岑今安。 氣質出眾的女人一筆一劃地在面前的合同上簽上自己的名字。 對面的男人語氣莫名:“岑小姐,你真的要背叛你的丈夫嗎?” “背叛?” 岑今安咀嚼著這個詞,自嘲一笑后緩緩而堅定地吐出一個字。 “是。” 她已決心背叛韓胤臣,轉投眼前人的藝術館,即便這人是韓胤臣的死對頭。 周妄笑了,收下合同,伸出手:“那麼,合作愉快,我的大藝術家。” 坐上回家的車,岑今安嘆了口氣,疲憊感重重襲來。 直到手機彈出一條消息。 韓胤臣:【安安,我回國了,你怎麼不在家,和朋友出去了嗎?】 看著關切十足的消息,岑今安嘴角勾起一絲諷笑。 一個月前,她偶然間在韓胤臣手機上看到一篇他發布的帖子—— 【我終其一生雕刻出你的復制品,卻不敢觸及你的萬分之一。】 帖子的熱度很高,岑今安點進去。 帖子中洋洋灑灑描述著他對一個女生一見傾心,最后卻看著她另嫁他人的故事。 沒什麼華麗的辭藻,卻將愛而不得的不甘淋漓展現。 最后,韓胤臣說:【我是藝術鑒定師,親手打造出一個仿品想要取代你,可直到現在我才發現,我只是在掩耳盜鈴。】 將那篇帖子看了十多遍,她本不相信,卻在無數次驗證下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 韓胤臣不愛她,只是將她當作另一個女人的替身。 殘忍的真相幾乎將心臟生生撕開。 岑今安從前以為,韓胤臣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運。 他幫她走出大山,他送她去學雕塑,擁有嶄新的人生。 可直到兩人訂婚她才知道。 原來自己才是韓胤臣手中的雕塑。 他用了八年時間,將她一點點雕刻成他的白月光。都市|現代|女性成長|言情3.3萬字 5 5035
猜你喜歡
溫馨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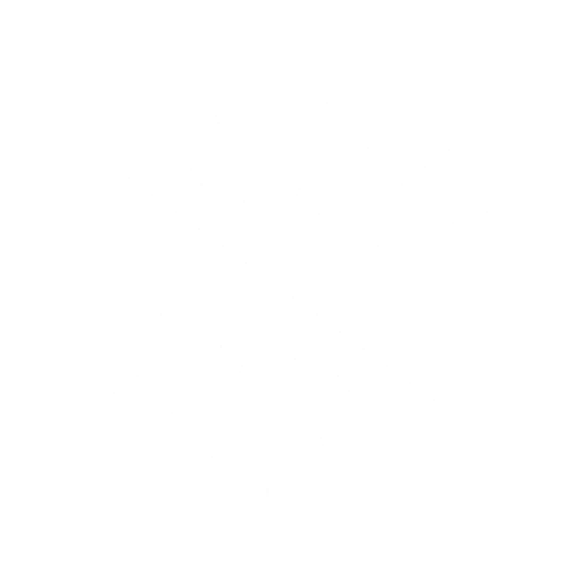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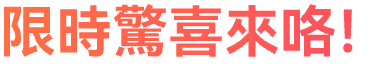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